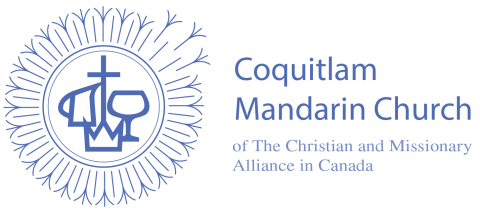亲爱的温吾德:
显然,你正在取得很好的进展。我唯一担心的是,如果你操之过急,反而会唤醒病人对他真实状态的感觉。你和我都清楚那种状态的真相,所以永远都不要忘记,一定要让这状态在他眼里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他的航向中引进了一些改变,让他脱离了围绕对头打转的轨道;但还必须让他想象,所有导致这种改变的选择,当然都是微不足道、可以挽回的。决不能允许他怀疑,他现在正在离开太阳,速度虽然缓慢,但却是在通往冰冷黑暗外太空的轨道上。
出于这个原因,我几乎是很高兴地听到,他仍然是一个按时上教会、按时领圣餐的人。我知道,其中会有许多危险,但什么都比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中断了最初几个月的基督徒生活要好。只要他继续外表维持基督徒的习惯,就可以仍然以为自己只是结交了几位新朋友、找到了一些新娱乐,属灵光景却和六周之前大致相同。只要他仍然这么想,我们就不必抵挡那种毫不含糊、彻底认罪的明确悔改,只需要对抗那种隐约感到最近有些不对劲的不安感觉。
这种隐约的不安需要小心处理。如果它变得过于强烈,可能会把他惊醒、搅乱全局。另一方面,如果你完全压制它,我们就会失去一个得分机会——顺便说一句,对头可能也不会允许你这样做。你如果允许这样的感觉存在,但却没有任其一发不可收拾地开花结果、变成真正的悔改,它就会具备一种无法估价的倾向。它会让病人越来越不情愿想到对头。几乎所有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有这种不情愿;但是,如果一想到祂,就会面对一团隐隐内疚的朦胧乌云,而且这团乌云还会越来越浓,这种不情愿就会增加十倍。他们会憎恨每一个能联想到祂的念头,就像陷入财务困境的人讨厌看到存折。在这种状态下,你的病人虽然不会忽略、但却越来越不喜欢他的宗教义务。他会在祷告之前尽量少想它,之后又尽快忘记它。几周前,你还得在他的祷告中引诱他脱离现实、分散精力:但现在,你会发现他向你张开双臂,几乎是乞求你去分散他的注意、麻痹他的内心。他将希望他的祷告是虚幻的,因为他害怕的是与对头真实的接触,想要的是让瞌睡虫来欺骗自己。
随着这种状况的逐渐稳固,你就可以逐步从用快乐诱惑病人的烦人工作中解脱出来。随着内心不安、又不愿面对,他会越来越与所有的真快乐隔绝。与此同时,习惯会使虚荣、兴奋和戏谑带来的快感变得不那么享受,但却更难放弃了;幸运的是,这就是习惯对于快乐的作用。那时你将发现,什么都能引走他那涣散的注意力。你不再需要去找一本让他喜欢的好书,用来阻止他祷告、工作或睡觉,昨天报纸上的一栏广告就行了。你可以让他在闲聊中浪费时间,不但与他喜欢的人聊喜欢的话题,还与他看不上的人聊厌烦的话题。你可以让他在一段很长的时期无所事事。你可以让他熬到深夜,不是热闹喧哗,而是在一个寒冷的房间里盯着一堆熄灭的柴火。我们希望他避免的所有健康向上的活动,现在都可以被抑制,并且不用给他任何补偿。这样,最后他就可以说:「我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生大部分时间既没有做应该做的事,也没有做喜欢做的事。」我自己的一个病人刚下地狱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基督徒用「没有祂,就没有什么是强大的 without whom Nothing is strong」(注:引自圣公会公祷词)来形容对头。 其实,「没有什么」本身就非常强大(Nothing is very strong)——强大到可以偷走一个人的最好时光,不是挥霍在甜腻的罪恶中,而是闪烁在沉闷的心思烛光里,晃荡在「不知道是何」和「不知道为何」的事情上,消失在手指的敲击和鞋跟的踢踏下,飘散在他不喜欢的口哨曲调间;或者迷失于漫长昏暗的幻想迷宫,但又缺乏情欲和野心为幻想加添滋味,只不过是偶然兴起的遐想。这个意志薄弱、脑子糊涂的受造物,在无所事事面前根本无力自拔。
你会认为这些都是一些很小的罪;毫无疑问,就像所有的年轻诱惑者一样,你渴望能够汇报一些惊人的恶行。但请务必记住,唯一重要的是你将病人与对头分离的程度。罪再小都无所谓,只要它们的累积效果能把人从光明推入虚空。如果打牌就可以得到一个人的灵魂,何必动用谋杀呢?实际上,通往地狱最稳妥的道路是平缓的那条——坡度缓和,脚下柔软,没有急转弯,没有里程碑,没有路标。
你深情的叔叔
思固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