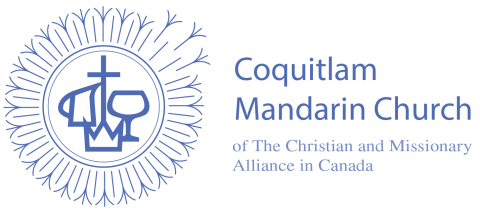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五日,海德与一支浩浩荡荡的宣教队伍在纽约会合。虽然远离了家乡和好友——一些好友十年后才得再聚首——但他旅途并不孤单。同船还有另五位宣教士:约翰-佛尔曼(John orman)夫妇、詹维尔(C.R.Janvier)伉俪、以及一位未婚的宣教士——莎拉-惠莉(Sarah Wherry)。十五天之后,船抵利物浦(Liverpool),预定在十一月底到达孟买。
莎拉-惠莉五十年后回忆道:「旅途中没发生特别的事,会使人想到约翰-海德日后会成为那样具有影响力的属灵人物。他很严肃,对信仰确是恭谨而认真,然而一点没显露出很有领导才能之势。他总是谦恭自持,虽然不是个孤僻的隐士,却也相当沉默。」这就是外表上的海德。内心里,他灵魂的汪洋中,却正刮着狂风暴雨。本来他自认是宣教事工的一只初生之犊,正要往刺激的历险旅途前进。他在各方面下过很多工夫,诸如受过广泛的神学训练,也曾基于宣教的热忱,为他最心爱的志业招募到一批新血;然而对他未来廿年传道生涯最重要的一项必备特质,他却疏于培养,而不够完备。
主所用的,祂必对付
因为海德虽然勤于发展自己的心智,却忘了上帝所要求的,亦即仔细下工夫熬炼自己的灵魂。往印度的旅程中,他彻底警觉到这件事。后来他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一位宣教同工彭温-钟斯(J. Pengwern Johns),说:「我父亲是传道人,母亲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她有一副动人的好嗓子,而且将它完全奉献给主。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要作宣教士,而且要作个『好宣教士』,我想成为一个卓越出众的伟大宣教士……。我立志要精通必须学会的各种印度方言,决心不让任何可能阻碍我成为伟大宣教士的事物阻挡我的路。那就是我的野心,一个把最重要的要素——上帝——给遗漏掉的野心。这样的野心也许并不完全出于肉体,可是大部分的确是。我爱主,想服事祂,而且想好好服事祂,可是其中,却有发自『自我』源头的野心存在。」
海德的父亲有位朋友也是传道人,他早年也满心渴望作宣教士,可是环境使他转向家乡牧会的服事。这位朋友得知海德要赴往印度,深表关切。海德说:「他很疼爱我,我对他也既敬又爱,我在纽约登上汽船,要往印度去开创我一生的事业,突然在卧舱里发现一封给我的信,一看是我父亲这位朋友的笔迹,逐打开展读。」
这封信不长,但里面的字字句句却敲在海德的心版上,掘入他灵魂的深处,在他自傲的灰土上燃起一把激愤不平的火焰。这位父叔辈的牧师说:「亲爱的海德,我将为你不停的祷告,直到你被圣灵所充满。」圣灵——这个字眼后来一直在海德眼前出现,直到他终于为圣灵所充满,而且真实感觉到它活泼的同在。
海德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我的自尊心受挫,我觉得万分愤怒,把信揉成一团,往舱房角落一扔,带着非常恼怒的心情上了甲板。他竟然暗示我『没』被圣灵充满!」
海德告诉自己,他是以宣教士的身份出来的,要是没被圣灵充满就出来,那就太放肆了;他位在最顶尖的高峰上,不是吗?很自然地,他自认已被圣灵充满。
海德继续说道:「而这人言下之意,却是我还没有装备好,不适合这份工作!我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内心激战不休。我觉得非常不舒服;我深爱写信的这个人,我知道他所过的生活很圣洁,心坎里,我相信他说的对,我不适合作宣教士。」
这场战争不是马上可以结束的,而海德生性也是不得胜利,绝不罢休。他回到卧舱,跪着找他扔掉的信。找到之后,把它抚平,「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我仍然觉得很气恼,然而那信念越来越强:我父亲的朋友是对的,我错了。」
阴霾消散,灵光闪现
在这种状况下,他渐渐接近相信的地步。又继续摸索了几天,其间海德的灵里简直是一团可怜的混乱。说起这场灵里的动荡,海德认为那是上帝的美意,在成就那位传道人的祷告。
「最后,我绝望地求上帝用圣灵充满我,我一这样作,内心所有阴霾一扫而空。我开始看见自己,目睹自己的野心是多么自私。这挣扎几乎一直延续到航程结束。不过在船抵达港口之前很久,我就下定决心,不论花什么代价,都要真正的被圣灵所充满。第二次高潮,是圣灵引导我对主说:即使到印度后我语言考试都通不过,即使我成为一个没人注意,默默服事的宣教士,我都愿意;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担任任何角色,可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得到圣灵。」
海德到达印度时,这场灵魂的探索并未终止。他应邀参加一次露天崇拜,讲员是位宣教士。那篇讲道一针见血的刺痛海德的良心,当时天上来的声音告诉他,耶稣基督是让人脱离罪恶的真正救主。崇拜结束时,一个英国人走到讲员面前问他,他自己有没有得到这样的救赎,这惊心动魄的问题,正是海德不敢面对的。「那问题击中我心房;因为如果是问我,我可得承认,基督还没完全救赎『我』这个人,因为我知道自己生命里还有一样罪没挪去。我明了到,如果我向人宣告,基督是完全的救主,可是却必须承认,这位基督还没使我脱离罪的捆绑,那实在是羞辱了基督的名。」
海德的灵魂陷入沮丧的泥沼中。自己宣扬完全的救赎,却没有经历过这伟大救赎的喜乐。他走回房去,关在里面,向上帝说,他必须在两件事中选择其一:「要不祢必须让我胜过所有的罪,特别是那项那么容易绊倒我的罪;不然我就回美国去作别的工作。除非我能在自己生命中证实福音的大能,否则我无法向人传福音。」
海德具备了蒙赦免的条件——认罪,他接着约翰书信中的信息,将自己的灵魂交托出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面对这个问题好一阵子,深知自己的灵魂正走在通向加略山以及战胜罪恶的道路上。
然后上帝轻声说话了,用保证的声音说,祂乐意,而且能够将他从一切罪疚中释放出来,并且他将在印度从事一项上帝所计划的圣工。全能者说话了,海德的生命焕然发出胜利的光辉。他说:「祂确实释放了我,自此以后我对这件事再也没有一丝怀疑。我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证实祂使我得胜,我乐于为此作见证,告诉所有的人,基督我主、我救赎主的奇妙信实。」
跟朋友彭温-钟斯叙述这番经历时,海德的脸上,闪耀着随之迸发的荣耀光辉。钟斯说:「我怎能忘记他告诉我这些事时的神情;说到自己的罪时那种形容不出的悲哀,提到基督的信实时那种美妙的笑容。」他对祈祷海德早年的回忆,先前曾在印度着书出版。
知所先后,果效必彰
灵魂上胜过罪之后,海德已预备妥当,可以开始工作。接下来又过了十二年,他才开始收割他祷告的荣耀庄稼。这段期间,他默默作工,没人注意,无人歌颂,平平凡凡地作一个平凡人,一面不住祷告,透过服事,全心信靠,奠下根基,使他日后在印度受尊崇,因祷告而名闻遐迩。
海德并非一蹴而几地登上祷告的金梯,而是经历无数危机四伏的黑夜,使灵魂锻炼得更坚强;经无数小时,回答似乎遥不可及,仍然低头祷告;历无数困境,信心之眼无法穿透时,仍然信靠。
海德在这些职分上任劳任怨,在最小的任务上尽忠职守,甘愿在上帝的事工里面作个无名的工人。起初海德并没建立什么丰功伟业,没有特殊的表现,也没显露出组织的长才。他有一点点重听,这无疑造成一些障碍,使他无法很快精通当地的语言。不过由于他温和的个性,很容易就与法洛兹普地区(Ferozepore district)的其它同工相处得很和谐。
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学习语言,但期间的情形我们所知不多。海德被分派住在达拉登(Dehra Dun),乌尔曼博士(Dr.Ullman)是那儿的老师。正当海德潜心学习,突然心中顿悟到一件事:他来印度是要把基督传授给那些心灵蒙蔽的印度人,而基督的荣耀,是从圣经中迸发的,可是他却还不真正了解圣经。
他立即决定要精通上帝的话,以便更清晰地把救主介绍给印度的芸芸众生。这使他和审核委员会之间产生了些许摩擦。我和一些在那些年中认识海德的宣教士谈过,譬如玛丽-康贝尔,他们都说他印度话学得很慢。其实并不是海德缺乏语言天赋,只是他因为研究圣经而忽视了语言的学习。当委员会责备他,甚至威胁要拒绝他加入这个工场,他只静静的回答:「我必须先作最紧要的事。」
以上的回答就是海德对整件事的看法,他觉得在谈其它任何事物之前,一定要先娴熟圣经。很多宣教士都证实,海德后来对这第二国的语言,也讲得很流利自如。他来到印度,为要教导上帝的话,他祈求圣灵把其中的真理展现在他眼前,让他能辨明。一旦这事成就,海德便备妥,乐于跨过前面横阻的一关关障碍。
一位听过他跟大批听众讲道的朋友这么写道:「他的晤鲁都话(Urdu)和将加比话(Junjabi)变得既正确又轻松自如,讲得跟他的母语一样好。在这一切之上,他娴熟地掌握了天国的语言,精通到一个地步,他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印度人,当他向他们展现上帝话语的真理时,这些听众都入了神。」
玛丽-康贝尔自己能讲好几种印度方言,使她能向二亿的印度人传道。她说,祈祷的海德在台上架势俨然,把他们的方言讲得如此轻松自如,流畅平顺,几乎和本地人一样。
语言虽障,人心不障
海德于一八九四年为他母校的大学杂志写了一封信,从中我们对他早期的工作,可略见一斑。
「去年(一八九三)一直到六月一日之前,我都在工作站学印度话,然后去了喜玛拉雅山区三个月……看到很多宣教士,乐在其中。其余时间,一直到十一月十五日,都在达拉登度过。我在那儿跟着乌尔曼先生学习……他是位好老师,他灵性上的影响,对我帮助极大。在几个月的探寻之后,有一份很明显的福分,降临到我身上。
耶稣的宝血,现在对我具有一种从前所不明了的大能。迄今之前的大部分冬、春天,都与印度传教士在各乡村里度过。昨天八名低下阶级的人,在其中一个村子里受洗。那是神所作的工,人纵然是祂的器皿,在其中所发挥的效用也是微乎其微。
请为我们祷告。我的印度话学得非常慢;在公开场合或交谈时,都只能讲一点。我不断在为班上同学祷告。今年,你们当中会有些人出来吧?工人太少了,太少了。」
就在这段期间,海德学习语言进展迟缓,一直无法流畅地跟当地人沟通,促使他向当地的总会提出辞呈,说自己由于重听,无法学习当地人的语言。
当地的总会立即接到从海德作工的村子来的请愿,村人请求他们不要接受辞呈。他们说:「纵使他永远不会说我们口里的语言,但他能说我们心灵的语言。」对这样的请求只能有一种答复,让海德继续在村人当中出现,就是答案。他一直和他们在一起,直到最后。
简陋账篷,甘之如饴
自始海德的工作就是在乡村宣教,其职责是把福音传给一些无法差派工人驻扎的乡村。海德忠于这份工作一直到未了。他多次的旅行,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有二十年之久,海德日复一日,经年累月地,带着他住的小帐篷,随同可用的当地同工,行过一村又一村,对着印度人的心灵,述说天国的话语。
因此他没有永久固定的居所,只有在各处宣教朋友家中借住的房间;所以他死前的遗愿,就是召募一笔基金兴建一幢宣教士之家,让工人可以安顿其中。这件事稍后将谈到,后来确实如他之愿而作成了。
不过海德有那顶帐篷,已觉十分自在舒适。他住在里面,睡在里面,带着它旅行,把它变成一间天堂大门口的休息室。有一封写给玛莎-葛瑞的信,又经她拷贝转给支助海德的各青年团体,里面可以看出他早期的一些活动及愿望。
庄稼已熟,工人何在?
这封写于费洛兹普,日期为一八九四年一月二日的信上说道:「上封信写时我还在达拉,在那儿待到大约十一月中旬,然后下来参加我们在路地安那(Ludhiana)举行的事工年会……再见到那些宣教士真好……年会本身有很多事要处理。宣教工作碰到诸多困难,在我看来,很叫人同情那些背负着事工重担的年长宣教士。我们早上的祷告会情况很好。路卡斯博士(Dr.Lucas)带了一堂,他说到要恒切地为祷告、为真道的事工献上自己……。
往乡村从事事工(探访村庄)的路,一直敞开在我面前,这也是我想作的工作。在费洛兹普这个地区,总人口有六、七十万,这边的乡村事工是针对城里二万居民以外的百姓。那些乡下人散布在数百个村庄、乡镇里面……这地区有两个宣教分部,位于哈克斯达(Huktsar)以及莫加(Moga)……教师(印度本国工人)整年都在这些宣教中心以及附近地区传教,我们这些喜欢巡回布道的人,就趁凉爽的季节,从这些中心,以及其它一些利于宣教的中心点出发,来往于各村庄乡镇之间。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向这六、七十万人传福音。工场上乏人悔改归主,但主差派了祂的工人来收庄稼。」
海德接着概略描述了他探访村庄时所有的助手。共有五位:他自己和另一位宣教士,以及三位印度同工。他说:「假想看看,如果芝加哥是个异教的城市,十五个人要向里面的一百五十万人传福音,你是其中之一;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不过我相信当你祷告求上帝赐下力量的时候,同时也会迫切地求祂赐下工人。」
这份迫切需要工人的负担,他也传递给支持他的那批年轻基督徒,他说:「今年,你们会里为什么不出来一人到海外工场呢?你们为什么不来呢?请不必回答我,要回答主。」
主内交谊,其甜无比
这一年,他和一个宣教士纽顿一家人同住。虽然他可以住在他平常去传福音的那些村庄里的任何地方。他和纽顿的女儿交往甚欢,她「受过慕迪先生芝加哥学院(Chicago Institute)和北春田学生聚会(Northfield Student Gatherings)美好气息的熏陶——这些都是圣灵满心喜悦,赐福多人的地方。)
一八九三年之间,他提及两项恩典:身体健康,没患热病;还有乌尔曼博士的影响,对他的属灵生活颇有激励。然后他说到:「感谢梅尔(F. B. Meyer)先生所着基督徒生活(Christian Living)这本书,以及你们的祷告……。」
想到伊利诺州基督徒青年事工团(Christian Endeavor)支持他的弟兄姊妹们,海德的传道人本性又显露出来了。他提出自己的见证说:「更加认识救主真好。不单单因为祂是我们的,更好的是,我们属祂。单纯地相信上帝的话,知道耶稣基督……祂自己把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承担在祂十字架的身躯之上;知道相信的人便有永生;知道因此便永远不再有咒诅;知道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子民——这是好的。在记忆中,最值得流连往返之处,就是那一个叫加略山的老地方,能记住它真是好。」
带着为印度祷告的负担,海德也力促青年事工团的朋友祷告,并学习「信靠上帝」这种令人喜乐的艺术,好为家乡带来更多的祝福,为印度倾注恩典。信的末了,他还附上其它人的短语,譬如:「有个人说他为异教徒感到很难过。一位贵格派老教友便反问他:『朋友,那你觉得你现在站在这里对吗?你找到了最适合你的地方吗?』」他也提及惠波主教(BishopWhipple)的话,说:『基督教事工里绝没有失败;唯一的失败就是不去作。』
他又提到阿姆斯壮将军(General Armstrong)的话:「若不是要奉上帝的力量完成不可能之事,基督徒还为了什么来到世上?」
这表明了祈祷海德的心志。他正奉靠上帝的力量每日奔忙,要藉着祂努力达成那不可能之事。后来在一封给玛莎-葛蕾的信上,他说到印度夏季炙人的酷热,唯有每天饮于神圣力量的泉源,才能继续走下去。
黑夜已尽,曙光乍现
接下来的一年是他个人得胜的一年,他写给麦坎密校刊的一封信对此有所描述。这段期间,我们发现他与拉霍尔的马丁博士(Dr.Martin)结为伙伴,在拉霍尔地区以及他原来的事工区工作。他说到自己的工作范围是「无数的村庄和乡镇,里面大约有一百廿万人,不过特别是在低下阶级的人当中,他们的人数我想可达二十万。他们是受人鄙视的农奴分子,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落魄到连自行死去之动物的死尸也吃。」
拉霍尔地区十个村庄里,大约有四百人接触过基督教。其中有几个人是在这一年,即一八九五年,接受洗礼。海德的工作就是要服事这些基督徒,以及这些村子里的其它人。
海德对带领印度人归主的快乐任务作了一番描述:「我对劳克(Lauke)这边的事工最了解,所以让我试着描述这儿的情形给你们听。这里低下阶级的基督徒教师,去年和邻村的一个人谈了一阵子,没有结果。我们的教师给了他一本新约圣经,因为这人比大多数人好得多,他能识字。前几天他告诉我,当他读到『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可十三31),他便信了。现在他自己也是我们的一位教师。」
从他抵达印度,在稳固的救赎盘石上立定脚跟的时刻起,海德一直为这些百姓的复兴祷告。就在这一年当中,他开始瞥见一点迹象,不过这工作要到西亚寇特大复兴(Sialkot revival)于一九○五年左右开始时,才算真的开花结果。
[一月份,上帝在此地赐给我们一小段复兴的季节,并持续了两、三个星期。就在这些聚会当中,我记得一个低下阶级的人,他的脸庞和心灵似乎都呼吸着上帝的话——真的是酣饮下去,那样单纯而清楚的表现,令我至今仍觉惊奇不已。]
最蒙祝福的,是他们开始学习祷告的那几星期的清晨祷告会,海德这么说:「在这儿你可以看到事工最令人鼓舞的一面。我们盼望在每一个有基督徒的村庄里,都能见到类似的事。」
但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非基督徒甚至还企图阻挠,不让挑水的人每天送水来给海德。他在自己的小帐篷里,把事情带到主面前,后来当地人又「偷我们的东西,威胁说要拉倒我们的帐篷,显然都是想把我们赶走。他们亦得逞把我们教师住的房子夺去,使我们在这里没地方安顿教师。上星期六晚上,有一位基督徒被殴,他们用骇人的言词恐吓所有的人,这真是困厄之秋,信心倍受考验之际。」
「为这些逼迫及自己需要的缘故,我在主宝座前长久祷告等候,感谢主,这宝座是恩典的宝座。」
那些日子,是海德灵命增长的日子。他学会如何不倚靠自己,而是信靠主。「自从到印度以后,上帝赐给我对于祂的一种新的了解。祂显然准备要祝福这些宣教士、工人、信徒及非信徒,特别是低下阶层的人。请用信心求上帝快快在印度赐下诸般福分。威尔德(Wilder)去年有时和我们在一起」——威尔德无疑是指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之父威尔德,毕业于普林斯敦大学(Princeton)。
「他二月的时候在拉霍尔,我们听说文温博士(Dr. Ewing)——我们在那边的大学的校长——得着五旬节的恩赐,而且其它人也开始进入。赞美主!」
流泪撒种,欢呼收割
接下的一年当中,约翰-莫特(JohnR.Mott)在旁遮普主持大学会议,海德在其中一场会议里,对学生发表一篇演说。这篇信息可以让人透悉海德的思想,也拉开晦蔽其灵魂的障幕。
他说:「有些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劳苦作工的果子,而内心渴望见到收成。」这无疑是从海德自身的经验有感而发,因为后来他提到,虽然他在一八九五年中曾带了一些人信主,翌年却一个都没有。
他又继续说:「我读过一个故事,有位苏格兰传道人,一个安息日的早晨,一群长老来见他,说觉得应该来和他谈谈,因为去年一年似乎成果甚少。这位牧师告诉他们,只有一个十二岁大的男孩成为稳定的会友(被接纳为可领圣餐者)。可是这名男孩来到牧师面前说:『牧师,你觉得如果我努力下工夫的话,可能成为传道人,或宣教士吗?』牧师说:『劳勃,你治好了我心里的创伤。是的,我想你会成为传道人的。』匆匆多年过去,许多人聚集要来听一位返回家乡的宣教士讲道。大批听众欢迎他,贵族士绅在他面前也脱帽致敬。他就是劳勃-莫法特(Robert Moffat),当年老教会里的那个男孩。他把一个未开化的国家带入文明世界,为教会增添了一个新教区,透过他的事工,许多野蛮人顺服了基督。忠心作工一定会有收成,不过,我们有可能只是『盼望』饥渴的灵魂能得着生命,『盼望』基督看见祂灵魂劳苦的功效而心满意足,我们只是这样『盼望』,就希望得着结果。但你曾为灵魂哭泣吗?……我有吗?『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一二六6)」
这些话对海德而言,是一首赞美的欢乐诗歌,是即将临到的胜利所预先发出的光芒。日后,祈祷的海德享受到一种特权,有几年他每年向上帝祈求要在那段期间内得着多少灵魂,上帝就尊重他的信心,赐下他所祈求的人数。
神怒短暂,神恩浩大
当海德重返乡村探访的工作,发觉没人信主,就召集两、三位同工,探讨其中原因,为什么似乎属灵的争战尝到了败绩。在写给迦太基大学校刊的信上,他向同学们剖明了心迹,他说:「今年各村庄里没有人信主,而去年有,原因何在?我们在探究其原因……。这探究的念头,是今天写这信时才兴起而加以确定的……。我们在想,明天就定为祷告日……如果这么作的话,我相信会很有收获。如果我们的心灵或者生活不对,而在上帝面前改正过来,我们会受到大大的祝福;即或祝福迟迟不来,那也是象拦住一道湍急的河水,一旦放开,必将带着巨大的能力倾泻而下。」
海德尝过神圣的爱,知道在上帝面前得胜的意义。他相信如果自己的心端正,上帝必会赐下信主的人作为回应。他肯定的说:「这是上帝爱的精髓,内心如果正确,祝福不可能撤回,只会递延;而让这种祝福迟延不到,是意味着,一旦它真的来到时,将四面八方淹没我们。」
海德当时不了解,他写的是一段预言,在往后十年间渐渐成熟、实现。他的祷告不断累积,忠心不断加增,努力在天上的银行要积蓄财宝;他笃定而确知,奖赏之日必到,神圣的祝福之流,要决堤泛滥,更新整个印度。海德是全能者的战鹰,他的灵魂受了神的祝福膏抹,就这样,他一面作工,一面带着信心的确据,等候恩雨的倾注。
他对神的荣耀信心十足地说道:「在基督里的生命是种奇妙的生命,有时这种经验只能用这句话来描叙——『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赛四十31)当人在枪林弹雨的攻击中,突然领悟到自己是站立在耶稣基督代付的赎价上,这时从那坚固的盘石中,要涌流出多么大的生命之泉!……我发现,一个人越接近耶稣基督,就会越迫切地作诗篇第五十一篇的祷告。」
海德一直跟着大卫重复的,正是这篇诗章中的祷告:「求祢按祢的慈爱怜恤我……求祢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求祢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祢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神啊,求祢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祢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我就把祢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主啊,求祢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祢的话……那时,祢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诗五一)
这就是海德,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他视为刚出道的工人,国度的见习生了。他已为个人宣教的事工,奠下健全而睿智的基础。这四年,他已投入在自己终身的事业当中;对这热爱的职志——乡村事工——他就此从未远离过。后来,他曾去很多的大会、教会、各个地区传递祷告服事的负担,但最后,他总是回到乡村探访的工作上,为主赢取众多的灵魂。